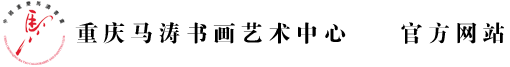古代书论扎根于仓领之说,它具有明显的合理核心。 这是太古的仓领们看到“仰视”、“博采众美”、“类物象形”、“因物构想”的文字创造的想法。书法培训先生介绍的这种方式,不仅符合太古时代的先人们比较熟悉的喜好榜样的原始思维特征,也符合古代文字创作和书写的特有象形性质。
卫恒《四体书势》中的《字势》具体描述古代文字创造“类物有方”的特质:
云——委员蛇爬布,星——远放光芒的稻草——苫垂
颖,山——it峨和连冈虫——妓女年轻,鸟——飞不了
杨……观察它,如果眼睛看得见。
证据是篆书中的“云”、“星”、“禾”、“山”、“虫”、“鸟”等字,它们确实生动富有象形性。 这个“有类”的象形文字,在大字体系统中,可以说是俯瞰,随处可见。 西周初期的《方鼎铭》代表性作品为例。 出土于辽宁喀左北洞村的青铜礼器,腹壁有碑文24字。 其中第一行的第一个字——“丁”,是笔肥圆的、对钉头垂直透视的直观描写——“亥”是笔细而可见、想要描绘动物“泵”的主干的第二行第三个字——“贝”,是类似单方面、对贝具象的视觉再现——第五个字——。 苯为颖,水稻谷大成熟,重穗垂下的第三行第一字——“朋”,经过很多抽象化,也能看到左右贝束的第四行第四字——“母”,以曲线为主笔,描绘女性膝盖的形状,胸前两点为双乳,显示性别特征的第六字——“尊”, 为了用双手保持酒坛的形象,左边是指示升降的记号(这是升标),两手高举…这一个具有不同的抽象性,但富有形象性,而且相当生动的造型,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对象世界的各种人事和形象。 许慎《说文解字序》“六书”之一的“象形”是:“象形者,描绘本身,并且遵循它”。 在《方鼎铭》和其他钟鼎器的碑文中,这样的象形文字非常多,它们是“类似物象形”“物构想”,对应物体的形状写成了线条,由此写成了“描绘该物”。 这个字在金文前面的甲骨文中更多见,在金文后面的篆书中也更多见,构成了它的象形的系统性质。
在这样的问题:许慎《说文解字序》中所说的作为自造字方法的“六书”,除了“象形”之外,可能还有“指事”、“意”、“形声”、“转注”、“借”。 大、小篆中的象形只是“六书”之一,除此之外的“五书”为什么还具有象形的系统性质呢?
马涛书法培训班级老师认为很多人都支持他,其实并非如此,只是看了看那块表,不在那里,忽然发现“六书”的不同,没有内在的联系。 本书认为“象形”不仅是“六书”之一,而且其精神复盖“六书”,统率着,几乎渗透到所有的文字中。 为了阐述这本书对中国的书法美学非常重要的观点,本书并非文学着作,但必须就其他《五书》一一举例说明:
指事,《说文解字)序》解释为“可见,可见”,意思模糊,但这种造字方法还没有印象深刻的可视性。 因此段注:“既是指事也是象形”的潘的涂《书法离钩六义》更具体地说是:
指事者把那件事弄直,除了象形文字之外,用手指也能识别。 在“树”或象形文字中加上“一”就是指“书”加上“1”,就是指最后。